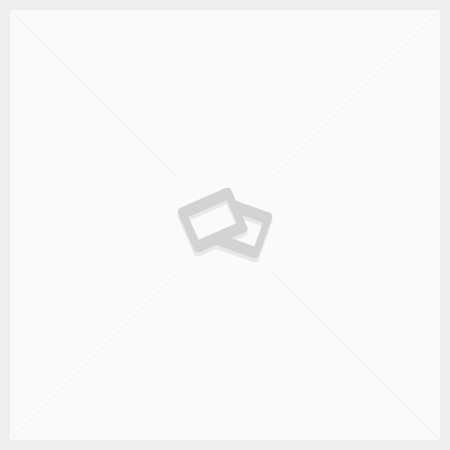曾遇過欺她、傷她、辱她的負心男人,
重活一次的慕雲月不再把情愛放首位,
卻不知某個傢伙已把疼她、寵她、愛她默默做了兩輩子……
慕雲月知道,自己曾同那個九五之尊有婚約,
但她和他相隔雲泥,還因故得罪對方不少,所以從沒奢望過什麼,
和前世渣夫了斷後便去自家別院安分過日子,
除了鄰家新搬來的傢伙有點煩人外,今生當真無不稱意,
真有什麼遺憾,大約就是不知上輩子那個冒死將她從火海中救回,又捨了心頭血,強行給她續了一年性命的恩人究竟是誰?
直到那天婁知許找上門,妄圖與她重修舊好,拿出婚書逼嫁,
「妳說,心裡還有哪個野男人!」
慕雲月掙不開他的手,以為這輩子又要毀在他手裡,
鄰居突然帶著一道聖旨現身,所有人都震驚成泥塑木雕,
衛長庚卻慢條斯理地抬起腳踩在婁知許臉上碾了碾,「你說誰是野男人?」
試閱
第一章 可笑的一生 生命如流沙般,從指尖一點一點消逝。 慕雲月捂著胸口,無力地靠在車壁上,朔風吹得她嘴唇發白,濃睫耷拉下來,隨料絲燈裡的火苗輕顫,宛如風雨中絕望掙扎的蝶,美好又脆弱。 車簾起伏不定,雪粒子從縫隙間鑽入,攜來路旁細碎的交談。 「這仗總算打完了,你都不知道我這大半年是怎麼熬過來的?要再拖一個月,我們一家老小可都得上閻王殿點卯了。」 「嗐,還不都是他慕家造的孽!誰能想到堂堂一個鎮國將軍竟會通敵叛國,也忒不是東西,對得起他祖上滿門忠烈嗎?得虧婁大人英明,早早就把叛軍剿滅,否則憑咱們盧龍城那幾面破牆,如何抵擋得住大渝的千軍萬馬?」 「要我說,這頭一份功勞還得是咱們陛下的。要不是他御駕親征,咱們這會子可都得被大渝擄去做奴隸了。」 那個年長的聲音似在回憶往昔,語氣頗為感慨。 「遙想十一年前,大渝興兵來犯,陛下也像今日這般,親自披甲掛帥,那時他才十六,前路還長著呢。大家都勸他三思,偏他不惜命,說什麼『吾既為王,食民之膏血而生,自當殫精竭慮,以吾之犧牲,換國之昌盛,誓與北境共存亡』。」 「說完他就衝進敵陣,一人獨挑七員悍將,連取七人首級懸於馬前,那風采、那氣魄……嘖嘖,真真是英雄出少年。把大渝那位常勝將軍嚇得都不敢說話!老夫當時還在後頭跟著一塊搖旗助威過呢。」 眾人聽得熱血沸騰,恨不能現在就隨那位少年天子去沙場馳騁一番。 忽有人問:「就是不知那位慕夫人現在如何?」 「父兄接連叛變,母親也畏罪自盡,整個慕家就剩她一人。聽說婁大人已經大義滅親,將她攆出侯府,她又身中劇毒,這冰天雪地的,怕是熬不過去。」 「呵,這就叫報應不爽,活該!早年她嫉妒家中妾室美姬比她得寵,害死多少人?就這麼死了還便宜她了!」 馬車拐過最後一道彎兒,直奔城南一座荒廢的祠堂而去,路邊的說話聲也逐漸消散在風中。 「姑娘,他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才會這樣說,您別往心裡去。」 馬車內,蒼葭倒了盞熱茶遞到慕雲月手中,指尖觸及她如何也溫暖不起來的肌膚,心尖也似被冰冷的刀尖劃了一下。 慕雲月笑了笑,也的確沒將這些放在心上。 人們只會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,旁人解釋再多都是無用。 慕家祖上有從龍之功,盧龍城便是蔭封授爵時得來的一塊封地,論條件其實一點也不好。 這裡地處西北邊陲,一無良田可耕,二無礦石可采,氣候還極為惡劣,一年到頭都見不到幾次太陽,根本住不得人。可偏偏這裡又是北頤同西北諸國矛盾的緩衝要塞,乃兵家必爭之所,一旦失守,後果不堪設想。 高祖皇帝為何將此地交予慕家?理由從這兒也可見一斑—— 他是希望慕氏能替他守住這道西北防線,護北頤子民安居樂業。 慕家也的確不負他望,以世代子孫血肉,鑄成了北頤永不潰敗的城牆。而這片荒蕪破敗的土地,更在慕家世代經營下,成了如今各國商貿文化互通的樞紐之地。 北頤人可在這裡安居,無家可歸的外族人也可來此處樂業,所謂血脈淵源、民族矛盾,一碗酒便可說開,誰也不會視誰為異類,街頭上照面還會相視一笑,頷首請對方先行。 可就在半年前,大渝興兵南下,把一切都毀了。 城外狼煙四起,城內民不聊生,大家都寄希望於汝陽侯府,願他們戰無不勝的慕家軍不日便能凱旋,再次為他們帶來穩定繁榮。 可最後盼來的,卻是七萬人絕塵而去,只有不到五千人負傷歸來,將帥皆亡,朝野震蕩。 婁知許拖著鱗傷之軀請命於鞍前,狀告慕世子通敵叛國,於千峰嶺一役中,以增援為名,行伏擊之實,慕侯爺知而不阻,害北頤軍大敗。 種種罪狀罄竹難書,每一樣都有通敵信函和戰俘口供為證,慕府內亦抓到不少細作,可謂鐵證如山,辯無可辯。 一夜之間,慕家就從人人敬仰的忠良世家,淪為過街老鼠,人人得而誅之。 民怨成鼎沸之勢,北境又戰火連天,北頤百年基業危在旦夕,沒有人能救慕家,更沒有人能救北頤。 直到兩個月前,紹乾帝衛長庚親自率兵出征,方才使民心歸附,山河無恙……可汝陽侯府還是沒了。 像一粒微不足道的沙,隨手就被從紙上拂去,從始至終都沒有人在意。 大家忙著慶祝,從帝京到盧龍,煙火放了三天三夜,慶功的醴酒把頤江都給釀透。可那幾封通敵密函究竟是真是假?那些戰俘細作又是何人手下?卻沒一個人肯過問,他們只想慶賀。 用一個真相未明的案子,就能將百年帥府推倒;造一段真假難辨的流言,就能把世代忠魂全部抹殺,任人踐踏。彷彿他們為這個國家流的血,根本不是血,丟的命,也不過是草芥。 起初,她還會同那些人爭吵,非要為父兄討個說法,可現在她卻是連張口解釋都懶。 「快到了嗎?」慕雲月偏頭去瞧窗外。 才出聲,喉間便爬起一串奇癢,她不由得攥緊狐裘,佝僂著猛烈咳嗽起來。 蒼葭忙幫她拍背順氣,摸出帕子給她擦嘴。 素白絹面一沾到她蒼白如紙的唇,瞬間鮮紅一片,縱橫的經緯間還嵌著幾塊發黑的血塊。 蒼葭瞳孔驟然縮起,努力克制住眼淚,卻壓不住聲音裡的哭腔,「姑娘還是回去吧,不過審問一個人,奴婢可以的,您何必親自跑一趟?為那起子骯髒折損自己身子,不值當!」 慕雲月卻搖頭,「有些路必須我自己走,有些仇只有我能報,誰也代替不了。」她氣若遊絲,聲音卻無比堅定。 陽光叫窗上的竹簾篩成一道道金色細線,在她臉上流轉,蒼白的面容和清澈的雙眼顯得尤為不搭,但也意外地耀眼,彷彿天上驕陽只是她的陪襯。 蒼葭是慕家的家生子,自幼跟隨慕雲月,對她再瞭解不過,凡是她打定主意,哪怕天塌下來也不會更改。 她捏緊帕子,唇瓣動了又動,蒼葭到底是歎了口氣,把勸說的話全嚥回腹中。 盧龍城南面那座祠堂,原是城中百姓為祭奠世代在北境拋頭顱、灑熱血的慕家人特地籌錢興建的,早年也是香火鼎盛,訪客如織。 小的時候,慕雲月還曾隨母親過來祭拜過,得了好些瓜果點心,都是城中百姓感念她父兄對北境的付出,專程送給她的。 而今是再沒有這些了,就連這座祠堂裡也只剩一片及膝的荒草和斷壁頹垣,鍍金銅像不知何時被人搬走,置物的木架也傾倒在地,香燭牌位四散而落,印滿腳印和蛛網,有幾個還摔成了兩截,黃幔從梁上扯落下來,在北風中無力飄搖,儼然一座「鬼屋」,連烏鴉都不肯打這兒經過。 明宇老早就在祠堂裡等候,他是慕侯爺留給慕雲月的暗衛,對慕家忠心耿耿。等人的當口,他已經把祠堂囫圇收拾了下,牌位也重新擺放妥當。 見慕雲月過來,他躬身行禮道:「姑娘。」 此言一出,縮在他身後一直咒罵不停的女子跟著一頓,但也僅是片刻,她就更加大聲地吵嚷起來。 「慕雲月,我便知道是妳!怎的?離了侯府後悔了?想讓阿許接妳回去?作夢!妳便是殺了我,我也是如今開國侯府正兒八經的侯爺夫人,識相點就趕緊把我放了,否則阿許必讓妳血債血還!」 木架底下,南錦屏被五花大綁丟在地上,朝她齜牙咧嘴。平日最愛乾淨的人,眼下卻蓬頭垢面,衣衫髒亂,倒跟這「鬼屋」十分呼應。 慕雲月不合時宜地在心裡感歎,忖著那句「正兒八經」,又忍不住譏笑出聲,「婚內通姦,無媒苟合,這也能叫正兒八經?」 南錦屏頓時啞了聲,卻還不肯認輸,一雙眼死死瞪著她。 蒼葭不悅地皺起眉,慕雲月卻跟沒看見似的,猶自踱步進屋,撿了張已經被明宇擦乾淨的官帽椅,施施然坐下。 這些年她追隨婁知許,經歷了許多,也改變了許多。 從前最是心直口快的一個人,路見不平定要上去插一腳,看誰不爽也是張口就懟,從不讓自己受半點委屈,如今卻也在時光裡磨平了稜角,學會了低眉淺笑,習得了算計人心,像一個標準的深宅婦人那樣,和別人虛與委蛇。 身上緋紅的綾羅綢緞,不知何時褪了鮮豔顏色,頭上的金銀飾物,也簡化到只剩一支固定髮髻的玉簪。